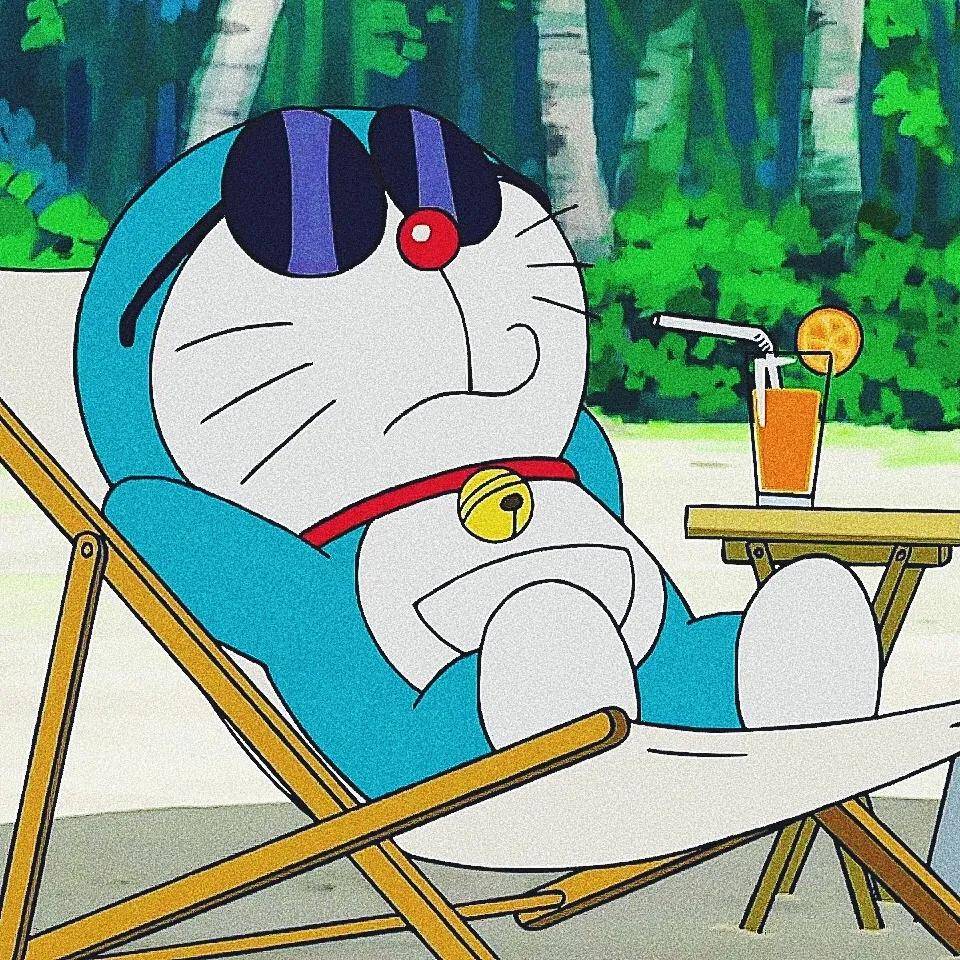科学的发展逐渐让人类从宗教的愚昧笼罩中苏醒过来,人类开始放弃宗教接纳科学,逐渐认同这个世界是由物理规则支配运行的,科学是认识客观世界最好的工具。从宗教到科学的转变,必然带来过去长久以来的基于宗教建立的思想体系的崩坏,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虚无主义
上帝已死
在宗教时代,存在的意义是一个很好解释的问题。世界先是一片混沌,而后有创世,造物主创造了这个世界,也创造了人类。宗教为我们解释了存在的意义:我们是被造物主创造的,我们与生俱来地带着某种意义来到世界。宗教为人类存在赋予了一种天生的、宿命式的意义,为我们制定了人生的目标,并以此约束人类的思想和行动。基督教说,世人生而有罪,我们此生便要忏悔罪责、信仰耶稣而得赦免与永生;佛教、伊斯兰教也不外乎如此。
科学让人类重新认识了世界,否定了造物者的存在,否定了天堂地狱的存在,也即否定了宗教关于存在的意义的解答。我们开始明白,人没有前世和来生,只有从出生到死亡的短短不到百年的时间。所以尼采才会说出“上帝已死”——这句话当然不是在谈论上帝,尼采想表达的是当时的人们普遍不再接受宗教里的上帝作为他们生命意义的来源和人生信仰。
存在焦虑
科学并不能替代宗教为我们解答人类和宇宙存在的意义,在宗教神学退位后,存在的意义便无法再得到解答。我们找不到人生存在的意义,也找不到世界存在的意义,我们不知为何存在在这里,只感到困惑、彷徨和绝望。思考这样注定要死且没有来世的人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这被哲学家称为“存在焦虑”。人类的存在没有意义,我们也无法找到世界的本质真相。这股思潮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现代化进程在19、20世纪的西方达到顶峰,并被称之为“虚无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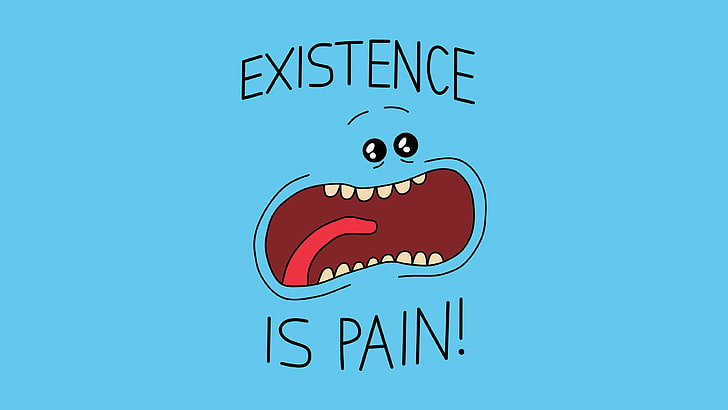
虚无主义大行其道,带来的是道德伦理的崩坏。一切都是虚无的,道德伦理也是虚无的,我们为何要遵循这些虚无的东西?毕竟上帝已死,遵守道德不会上天堂,犯下罪责也不会下地狱。面对这样的局面,人类急需对存在的意义找到新的解答。
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是对存在的意义的一种全新的思考。存在主义将存在放在首位,在此之上重新构建了意义。存在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是让-保罗·萨特(Jean-Paul Charles Aymard Sartre);“存在先于本质”是他的经典名言,他告诉我们,人首先存在,而后才有意义。
存在先于本质
一把刀可以用来切割物体,“切割物体”就是刀的意义和本质。人类需要切割物体,所以发明了刀——人类赋予了刀的意义和本质,人类是刀的造物主。这个例子说明了事物的本质可以先于存在——“切割物体”的意义总是存在的,而作为实体的刀不必一定存在。这种质朴的思想自柏拉图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哲学家称为“本质主义”:世界上的事物总是都该存在本质属性的。
我们可以轻松说出一把刀存在的意义,但我们是否可以追问所有事物的本质和意义呢?宗教可以编造一个逻辑自洽的思维体系来解释这个问题,但科学不能。从科学的角度看并没有一个“造物主”来创造世界,我们只能知道我们就存在于此。对此,萨特告诉我们“存在先于本质”,将本质论颠倒了过来。我们并非因为某种意义而被创造出来,我们的存在本身并无意义,存在才是我们的第一性。
追寻存在的意义
萨特论述存在先于本质,承认人类本身的存在并无意义,并非是要走向虚无主义,而是要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应当自己寻找、自己选择。既然我们的存在没有天生的意义,那我们的人生就是自由的,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以此来追寻我们存在的意义。
萨特的这番论述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这里谈论到的自由不可避免地带有自我主义的色彩。我们的选择真的是完全自由的吗?萨特作为一个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能抛开社会关系谈论个人的绝对自由。萨特认为,我们的选择当然会影响到他人,因此我们的选择不仅应当为自己负责,也要为他人负一定的责任。我们为自己做出选择时,就无法避免与他人的选择产生冲突——“他人即地狱”。但萨特对此并不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总有一些普世的价值使得我们都倾向于做出对的选择,就是对自己和他人都有益的选择,使其对整个社会的收益最大化。
存在主义也使得我们重新思考“意义”。上一段论述了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我们自己的的选择总是会和他人、社会和环境相互作用影响。因此意义也就不是一个终极的一成不变的概念了,而是每时每刻随着我们的选择在不断发展变化。意义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了。
结语
存在主义改变了我们对人生意义的追问,让我们从宗教式的、宿命式的意义枷锁中解脱出来,在承认虚无的基础上,我们意识到我们是自由的,是自己意义的主宰,为“意义”重新赋予了积极的色彩。